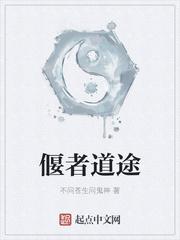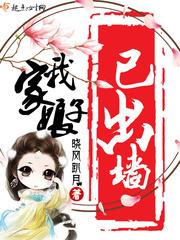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番外 序二 与浪潮同热 贾植芳(第1页)
番外:序二:与《浪潮》同热贾植芳
拿到《浪潮》校样时,我正就着煤油灯改学生的小说稿,油印纸的墨香混着灯油味飘过来,一下子把我拉回三十年代。那时我们在上海办《七月》,也是这般几张油印机,一群年轻人,凭着一腔热血,把对家国的牵挂、对文学的执着,全印在粗糙的纸页上。
许成军这小子,我早有耳闻。有人说他“愣”,敢在课堂上跟教授辩“文学该不该沾烟火气”;有人说他“轴”,为了找老匠人采访,在工厂门口蹲了三天。今见《浪潮》,才知这“愣”是不随波逐流的劲,这“轴”是对文学真心的痴。
创刊词里那句“钢枪护山河,笔杆守魂魄”,看得我心口一热。我这辈子,见过枪林弹雨,也挨过文字狱,最明白“笔杆也是武器”的道理。时下有些“文化人”,躲在书斋里唱高调,要么把西方的月亮夸得比中国圆,要么把本土的东西贬得一文不值,忘了文学该为谁写、该说什么话。《浪潮》不这样,它批“媚外软骨”,也赞“守根硬气”,字字句句,都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:有热血,有骨气,有脑子。
我读刊里的文章,没有掉书袋的理论,没有装腔作势的抒情。有篇写武康路梧桐叶的,说“叶子落了还能护根,人可不能丢了魂”,多实在!还有首诗,写工人师傅修机床,“扳手拧的不是螺丝,是日子的紧”,这才是中国的诗,从生活里长出来的,带着汗味、铁味,还有人心的温度。
有人说校园刊“小打小闹,成不了气候”,我偏不这么看。当年《七月》不也是从油印开始,一步步成了文坛的“硬骨头”?《浪潮》现在三千册,不算多,但每一本都带着年轻人的真心,能传到一个是一个,能点燃一颗心是一颗心。许成军说要“做破冰之浪”,好!这冰,就是文坛的惰性、思想的僵化,就得有年轻人敢去撞、敢去破!
我老了,写不动长篇大论了,但看见《浪潮》,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。我没什么大道理可讲,就想跟成军和社员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:好好写,别怕!文学这路,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,但只要心里有火,笔下有真,就别怕浪小——浪再小,也能聚成潮,能掀动人心,能改变点什么。
这序,我不写客套话,就写我的真感受:《浪潮》这刊,我喜欢;许成军这伙年轻人,我佩服。往后,我这老骨头,也愿跟他们一起,为这浪潮添把劲,同热、同奔涌!
- 龙王殿齐天齐天沈秋水
- 看过人间月色 江清雾江清雾季晏离
- 师娘赶我下山苏麟夏冰语
- 陈平,苏雨琪龙王令陈平
- 温火【伪骨科、np、高H】尹汝月
- 唐墨免费阅读唐霜墨承白
- 夜云天萧澎无敌傻太子
- 看过人间月色恰逢暮雪又白头江清雾季晏离
- 看过人间月色 江清雾免费观看江清雾季晏离
- 看过人间月色夏之宁江清雾季晏离
- 官道之权势滔天文林峰杨星宇
- 看过人间月色江清雾季晏离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江清雾季晏离
- 清禹的小说是什么蒋禹清景衍穿越
- 从神墓挖出的无敌老祖萧晨
- 沈归舟陈穆愉最新章节列表沈星澜陈穆愉
- 看过人间月色江清雾结局江清雾季晏离
- 江清雾季晏离看过人间月色最新章节字数江清雾季晏离
- 陆尘李清瑶免费阅读全文无弹窗陆尘李清瑶
- 女神的超级狂医十年萤火杨洛柳雨薇
- 冥都监狱赵平安齐天娇
- 林峰宁欣林峰桃红
- 看过人间月色江清雾第九章江清雾季晏离
- 等你在清华全文免费阅读林陌安妙薇无弹窗
- 狂兽战神 笔趣阁司空靖苏月汐
- 威震四海佚名
- 无敌六皇子免费阅读小说最新章节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免费全本阅读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免费阅读最新更新云铮沈落雁
- 云铮沈落雁小说无敌六皇子最新章节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主角云铮沈落雁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小说最新章节列表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最新更新章节免费阅读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全文免费阅读无删减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刚刚更新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小说免费完整版云铮沈落雁
- 盖世狂徒萧北辰免费阅读萧北辰慕紫嫣
- 无敌六皇子小说完整版本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最新章节无弹窗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全文阅读最新更新云铮沈落雁
- 执掌风云萧峥免费箫峥小月
- 无敌六皇子免费全文阅读小说云铮沈落雁
- 云铮沈落雁无敌六皇子小说免费全文无删减阅读云铮沈落雁
- 无敌六皇子完整小说云铮沈落雁
- 棺香美人小说阅读李阳黄九爷
- 小说妖孽下山师娘师姐太宠我楚凡林泰然
- 我在精神病院学斩神TXT下载林七夜
- 无敌六皇子免费全本小说云铮沈落雁
- 执掌风云萧峥陈虹陈虹萧峥
- 宋惜惜战北望六月将门弃妇又震慑边关了
- 无敌六皇子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云铮沈落雁
- 背叛我后,男友倾家荡产了醒醒神
- 被拐姐姐直播复仇如家的莫老道
- 和闺蜜一起嫁进豪门后啊熊熊的家
- 距离有些远李敏吕青
- 戒灵九霄爱吃炖菜烀饼的渊如海
- 拒绝女神就变强,舔狗系统气疯了于冰心
- 女修不孕不育?这我专业啊!太子画漫
- CEO亲手裁掉了公司唯一的钥匙零零落落的夕晖
- 女多男少,我是全校女生的白月光丁阳凌心甜
- 未来被剧透后,人类集体摆烂了哎哟蜗趣
- 新婚夜走错房被军官小叔亲哭了颜墨
- 开局怒怼朱元璋,我活下来了公子枫
- 抢我身份重生嫡女将侯府挫骨扬灰再不咸鱼就老了
- 打累了崽崽我要回家喝奶了:芽芽陈煜宋朝朝青梧映
- 考公三战三败,意外穿越成流落民间的太子小米粒滴妈
- 他用我的钱养小三冰摇红莓黑加仑105
- 穿越一念关山:我哥是宁远舟爱吃剁椒三明柿的罗塔
- 伪善腹黑乖乖女,她逆来顺受佚名
- 退休战神在都市吉甫
- 梦巡万界德颐老哥
- 从轮回空间开始的面板顾衍
- 再也不做你们家的“奴”叙述良言
- 神雕:尹志平从多子多福开始无敌司源
- 灵道纪笑傲余生
- 用你的白月光爱别人夏沫桃子
- 职业白月光翻车?四个前夫痴缠我瞿颂安殷岐裴
- 觉醒顶级冰系,然后一路无敌!极暗诞于光
- 带着乙女黄油穿排球喵喵炒饭机
- 大小姐重生选夫,小小硬汉拿捏拿捏福代代
- 人在废丹房,我以丹药证道成仙!吃猫的鱼仔
- 影去冬来佚名
- 王府里来了个好孕小王妃虎金金
- 带著空间在五十年代满地白霜
- 快穿:重回巅峰安楠赵卓先
- HP白眼给你顶级魔药天赋杰莱尔普林特
- 一胎又一胎,说好的禁欲指挥官呢?唐甜甜
- 冠盖满京华府天
- 婚心如玉:权少,宠妻上天安凌晓
- 寂寂秋风知岁晚:汀兰陆知行阿若后续爱吃甘蔗牙崩掉
- 欢乐颂:邱莹莹网店创幸福邱莹莹樊胜美